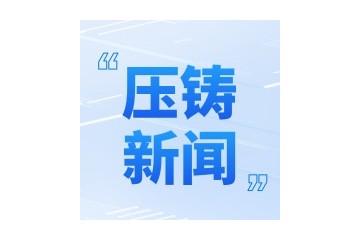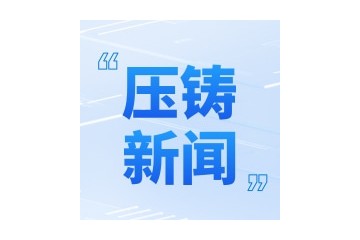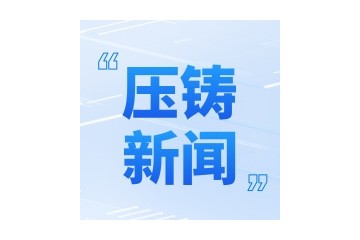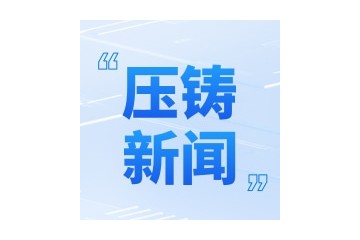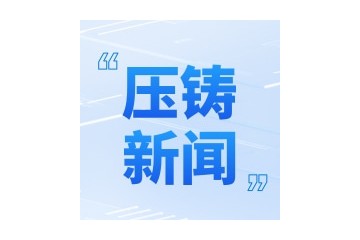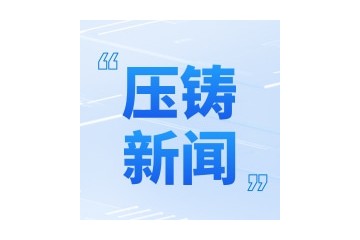正是由于在LME庫存體系的運作中,倉儲公司和持貨商都能夠為自身牟取一定的利益,才形成了如今這種看似“雙贏”的局面。不過,這種庫存體系對鋁行業的負面影響也在逐漸生成。
去年年末,LME掀起了一場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倉儲之戰,鋁庫存在短短一個月內從450萬噸激增到500萬噸,倉單注冊與注銷空前活躍。從今年9月中下旬開始,LME鋁庫存再度發力,重新站上505萬噸的記錄高位,注銷倉單數也高企在160萬噸上方,占到總庫存的30%以上。一邊是倉單注銷規模的龐大,另一邊是不見降低的庫存,這似乎不符合倉單“注銷”的理論含義,但是如果我們理清楚LME鋁庫存體系的運作狀況及其背后的利益驅動,就會認識到海外金融與貿易巨頭在如今LME市場上的地位舉足輕重,并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看清現行庫存體系對鋁行業的弊端,從而為未來可能的制度變革打下基礎。
LME鋁倉庫運營及規則
LME目前在全球擁有700多家核準貨倉,用于銅、鋁、鉛、鋅、鎳等各種金屬的存儲及交收。這些倉庫分布在北美、歐洲及亞洲等地的33個港口與地區,其中32個存放著可用于交割的鋁庫存。在LME倉庫的日常運營中,有三條體系規則最為關鍵。
第一,倉庫所有權不歸屬LME,具體的經營活動由不同的倉儲公司負責。LME只負責前期對交割地址、倉儲公司及具體倉庫的審核與批準,倉庫選定之后,日常的管理與運作包括倉庫的盈虧完全由各自的倉儲公司擔當。這也就意味著,只有具備相當資質的倉儲公司,才能在滿足LME嚴苛要求的基礎上,成為其倉儲運營商。目前LME的倉儲公司基本都是一些從事金屬貿易多年、具有豐富經驗、信譽卓著的專業機構,如Metro、Pacorini等。它們為現貨持有人提供倉儲交割的地方,從中收取租金,以實現倉庫營運利潤。
第二,LME倉庫規定了每日的最低出庫量,超過90萬噸的鋁倉庫最低出庫量為3000噸,未超過90萬噸的僅需1500噸。也就是說,只要倉庫達到了每日的最低出庫量,即便仍有注銷倉單積壓,也可以放慢節奏,推遲出庫。這對于倉儲公司來說,能夠帶來更多的租金收入,而在遠月升水的期現結構下,即一般情況下的正向市場,現貨持有人也樂意延長存儲時間,并不著急出庫,因為近低遠高的合約結構能夠使得手持現貨的空頭,在遷倉的過程中得到遠期升水的收益。在現實情況中,只要市場恢復到一定程度的期貨溢價,LME多數賣方就會重新注冊已注銷的倉單,而這只需要簡單改變標記在庫存上的標簽就可以實現。
如此看來,倉儲公司與賣方都有維持高庫存的動機,而如今的LME市場上這兩者的身份往往出現重疊。這里就需要引出第三條規則,即在實物交割過程中,LME合約規定,交割倉庫和交割金屬的品牌只能由賣方決定,買方無權選擇。在這樣的規定下,交割的金屬可能放在買方裝運極不便利的地區,又或者交割的品牌不滿足買方的特定需求。此時,買方只能自己尋找其他手持倉單的賣方,努力說服其調換倉單,并承擔不同品牌、不同等級之間的升貼水。由于倉儲公司與賣方可能歸屬于同一個機構,交割地點與品牌又都由賣方來選擇,這就使得一些暫時不想出貨的貿易商,故意把交割地點安排在早已經排起長隊的交割倉庫,或者選擇一些買方不方便拿貨的地區,再由買方自己去調換倉單,從而達到拖延實物出庫時間的目的。
由此可以看出,在現行的LME庫存規則下,賣方與買方的權利實際上是不對等的。賣方出于各種利益的考慮,即使已經注銷了倉單,也可以繼續保留庫存,而買方對此只能被動接受,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注銷倉單增加的同時,庫存卻沒有明顯下降。
看似“雙贏”的利益驅動
基于LME更有利于賣方的庫存體系,近年來,國際金融與貿易巨頭紛紛收購或控股大型金屬倉庫運營商,以獲取多重收益。這其中包括高盛、嘉能可、摩根大通等傳統的大宗商品交易商,它們如今已成為全球電解鋁市場上的中堅力量,對鋁價的影響力絲毫不亞于俄鋁、美鋁等鋁業大亨。在LME的股東組成中,高盛、摩根大通、瑞士銀行等金融機構都是重要的成員。特別是高盛,在2009年到2011年間,將所持的LME股份從30萬股猛增到123萬股,目前已是LME最大的單一股東,占LME全部股票的比重達到9.5%。高盛金屬交易業務部門的主管斯蒂芬·布蘭頓-斯皮克,同時也是倫敦金屬交易所的董事會成員。
這些投行們一邊掌握著LME日常經營的生殺大權,一邊又熱衷于購買倉庫,在部分地區,高盛、嘉能可等機構旗下的倉庫已經占到壓倒性的份額。例如,在荷蘭弗利辛恩港的39個LME倉庫中,被嘉能可控股的金屬倉庫運營商Pacorini Metals就擁有其中的37個;在美國底特律,高盛的子公司Metro也擁有總數37個倉庫中的29個。盡管LME規定,同屬一家母公司的倉儲部門與其在LME交易的部門之間,一定要建立嚴格的“防火墻”,但是在多次的市場表現中,嘉能可、高盛、摩根大通等機構的交易頭寸卻與各自倉庫里的庫存和倉單變化有著驚人的配合。去年12月21日,在LME每月“第三個周三”的重要交割日,荷蘭弗利辛恩港鋁倉單的注銷數從此前的0突然增加到14.5萬噸,第二天繼續增加到50萬噸,這些被注銷的庫存數量恰恰對應了當時的空頭倉位規模,而該倉位又恰好被Pacorini的母公司嘉能可持有,彼時弗利辛恩也只有Pacorini一家LME倉儲運營商。這中間的關聯不言自明,嘉能可作為空方并選擇了交割,多方則是摩根大通,它在荷蘭鹿特丹也擁有一座Henry Bath倉庫,其買入交割獲取的鋁錠據悉被運到了這里。
而在當前LME市場繼續保持著的遠月升水期現結構下,交易商又可以很輕易地通過買入近月、賣出遠月而獲利,并將金屬庫存鎖定在倉庫中,以獲得融資交易的收益。事實上,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至今,海外金屬倉儲業的生意就一直很紅火,這除了歐美地區低利率的貨幣環境刺激外,對于倉儲公司和持貨商而言,似乎也是一件“雙贏”的事情。
對倉儲公司而言,它們可以獲得的收益主要來自于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倉庫租金收入。今年年初,LME鋁倉庫租金為每日每噸0.41美元,從4月份開始已經提高到了0.45美元,上浮10%。按照目前LME總庫存規模505萬噸測算,LME倉庫單日的總租金收入就高達230萬美元。在這其中,個別大型倉儲公司的收益也非常可觀。在LME鋁倉儲的32個港口與城市中,美國底特律與荷蘭弗利辛恩的庫存規模排名前兩位,高盛的Metro和嘉能可的Pacorini分別占到這兩個地區庫存的80%和95%,底特律和弗利辛恩目前的庫存規模分別在145萬噸和126萬噸,由此測算得到,Metro在底特律的單日租金收入可達到52萬美元(145萬×80%×0.45美元),而Pacorini在弗利辛恩的單日租金收入也接近55萬美元(126萬×95%×0.45美元)。
第二,如果倉儲公司本身又隸屬于高盛、嘉能可這些投行,庫存貨物不屬于它們,但已經被其他持貨商用作向其融資的質押,那么對這些金融機構而言,從融資交易獲取的利息又是一筆豐厚的收入。只要當前鋁價維持遠月升水的正向市場結構,銀行為現貨商提供的庫存融資業務就有利可圖。
第三,如果倉儲公司及庫存貨物都歸屬于某一金融機構,即倉儲公司與持貨商的身份發生重合,那么它們還可以獲得如今在鋁現貨市場上的高溢價。以嘉能可為例,作為全球性的大宗商品交易商,其在第三方金屬交易中(除了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直接交易以外)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鋁近40%、銅50%、鉛45%、鋅60%的市場份額都由其控制。全球最大電解鋁生產商俄鋁40%以上的產品也是銷售給嘉能可,二者在今年已經簽訂了一份長達7年的長期銷售合同,嘉能可在LME基準價格的基礎上給予俄鋁穩定的溢價,隨后又可以轉手在現貨市場上以更高的價格售出。
事實上,如今海外市場上現貨鋁的高溢價盛行,嘉能可一方面將自有的鋁錠鎖在LME倉庫中,使實體市場上的現鋁供應維持低位,保證現貨鋁的高溢價狀態得以持續;另一方面,又可以在現貨鋁的溢價上升到一定水平時,隨時拋售獲取溢價收益。而今年年初至今,在歐洲、美國及亞洲多個國家與地區的現鋁升水報價中,同比增幅高的可達90%,接近一倍,而低的也有30%的上漲。
對持貨商(指一般的現貨生產企業,如美鋁、俄鋁等)而言,它們可以獲得的收益主要來自于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持貨商之所以愿意持續不斷地把庫存運入LME倉庫,主要是因為鋁庫存可以作為抵押,從銀行獲得融資支持。根據前文分析,在LME鋁遠月升水的期現價格結構下,銀行也樂于為現貨企業提供這種業務。銀行獲得了利息收入,而現貨企業也以較低的利率得到了維持日常經營所需的資金流。
第二,它們同樣可以獲得來自現貨鋁高溢價的收益,這與上文嘉能可同時作為倉儲公司和持貨商的情況一致。
正是由于在LME庫存體系的運作中,倉儲公司和持貨商都能夠為自身牟取一定的利益,才形成了如今這種看似“雙贏”的局面。不過,這種庫存體系對鋁行業的負面影響也在逐漸生成。
現行LME庫存體系的弊端
在LME倉儲公司與持貨商“互利互助”的背后,鋁庫存高企難下,現貨市場上鋁溢價保持高位,這已經對全球的電解鋁行業產生了不利影響。
1.危及鋁下游消費行業
受現行LME庫存規則的限制與融資交易的利益驅動,大量的鋁供給都進入了LME倉庫中。據保守估計,目前505萬噸的LME鋁庫存中65%以上都被融資交易鎖定。這就導致了現貨市場供應的緊張,海外現鋁市場上的升水也因此創下紀錄新高。CRU數據顯示,今年9月荷蘭鹿特丹關稅未付與已付的升水平均為213、275美元/噸,遠高于去年同期的130、195美元/噸;美國中西部P1020升水為11美分/磅(折合為242.5美元/噸),去年同期為8.13美分/磅(約180美元/噸);亞洲地區,日本到岸現貨升水為225美元/噸,新加坡P1020入庫升水為175美元/噸,同樣顯著高于去年同期的117美元/噸與93美元/噸。9月到中國的鋁錠進口升水也創下了前所未有的高位,達240美元/噸,而去年同期僅為120美元/噸。在LME金屬價格低迷的情況下,升水的穩定激增使其占LME鋁價的比重上升到了14%,而2009年時僅為4%。
在現貨鋁錠升水暴漲的同時,下游增值產品制造商卻沒有能夠獲得同樣的溢價收益。據CRU統計,在過去三年中,德國北部交付的鋁坯(鋁錠初級加工品)升水上漲了27%,同期,鹿特丹關稅已付現貨鋁錠的升水漲幅則高達280%。鋁制品商對終端消費者的供應合同沒能涵蓋現貨鋁的溢價變化,因此無法將當前的高升水傳遞給最終的消費領域,只能單方面承擔持續上漲的原料價格。
與此同時,鋁錠下游消費商則苦于在LME倉庫“排長隊”等待提貨。由于融資交易的持續,持貨商一旦把鋁錠運入LME倉庫,就不會輕易移出,而倉儲公司也傾向于鼓勵持貨商進行長時間的存儲,對鋁的注銷倉單也是維持在一個較低的裝卸率。按照目前90萬噸以上倉庫每天最低3000噸的出庫速度,弗利辛恩港已被注銷的鋁錠接近85萬噸,這需要耗時9—10個月的時間才能完全運出,底特律同樣需要大半年的時間才能把鋁錠交送到今天買入交割的下游消費商手上。
2.掩蓋了鋁行業真實的供求關系
一般而言,某種商品庫存的高企往往反映了供給過剩,而現貨升水的上漲大多體現的是供不應求。令人困惑的是,在如今LME鋁市場上,高庫存與高升水同時存在,這已經嚴重干擾到投資者對鋁行業供求關系的準確判斷。
由于融資交易的存在,大部分鋁錠供應都被鎖在LME庫存中,人為造成了現貨市場供應的緊張,導致了高升水的出現。也就是說,當前鋁需求并沒有像高升水反映的那樣強勁,而是應有的供給被抽離出了實體市場。事實上,今年前三季度,全球原鋁消費同比僅增加了3.3%,明顯低于去年全年9.8%的增幅,而供給增幅略高于消費,整體供需平衡仍然表現為過剩。
3.誘發逼倉事件,擾亂正常的市場秩序
由于高盛、嘉能可等機構有能力通過控制貨物出庫時間、調整注銷倉單、抬高現貨升水等方式,掩蓋真實的供求關系,近年來這些機構主導下的LME逼倉事件頻頻發生,對金融市場的正常交易秩序造成了不良影響。以今年5月爆發的LME銅逼倉事件為例,當時江銅等現貨商、投資資金以及融資銅在LME市場上的空頭大量集中,被嘉能可、摩根大通等機構迅速盯上。這些機構立即采取擴大注銷倉單、限制庫存出庫以及大量采購現貨銅等方式,拉高現貨價格,迫使期現價差不斷擴大,企圖誘導倫銅上揚,令空頭虧損出局。盡管這場逼倉風波在江銅等現貨商高調宣布向LME交割銅之后得以平息,但在現行庫存體系下,嘉能可等機構擁有的翻云覆雨的能力,不能不讓市場有所忌憚。銅的這場逼倉現象,也可以輕易地復制到鋁、鋅、鉛等金屬上,未來類似的逼倉事件或將頻頻發生。
綜上所述,LME現行的庫存體系,一方面有來自于倉儲公司、金融機構及持貨商的利益驅動,另一方面又暴露出對鋁行業的種種弊端,兩者孰重孰輕似乎不難判斷,難的是如何改革已有的體系與制度。改革從來都不是易事,但是認識到問題的存在,也算是開啟了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客服熱線:
客服熱線: